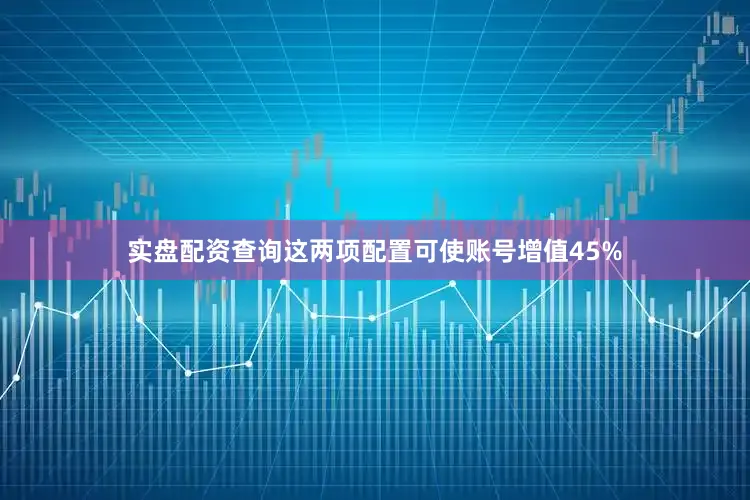图片
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,可是心里直翻腾,开不了口。——老舍《鼓书艺人》
假如我是一只鸟,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——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——穆旦《赞美》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?请写一篇文章。要求:选准角度,确定立意,明确文体,自拟标题;不要套作,不得抄袭;不得泄露个人信息;不少于800字。
当老舍笔下鼓书艺人欲歌无言,艾青化身嘶哑之鸟,穆旦伸出带血之手拥抱大地——他们共同昭示着一种精神困境:在苦难与创伤的茫茫汪洋中,语言之舟往往触礁沉没。然而正是这些失语与嘶哑,构成了苦难最沉痛又最真实的回响;那失语处最深的寂静,恰是灵魂最痛彻的呐喊。创伤常使语言失效,沉默却非全然虚无。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“心里直翻腾,开不了口”,这凝滞的瞬间,是巨大苦难的无声证明。那无声的翻腾,正是无法被语言打捞的创痛深渊。如同史家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剖白肠一日而九回的哀恸,文字终难穷尽屈辱之万一,可正是这无法尽言处,才真正映照出个体苦难的深重。沉默并非空洞,它是语言无法承载的伤痛所留下的印记,如大地深处无声的惊雷,以无形之力震撼着所有能够感受的灵魂。当完整表达之路被阻断,破碎、嘶哑的声响便成为珍贵的抗争。艾青化身之鸟以“嘶哑的喉咙歌唱”,明知声音已损,却仍以伤痕累累的喉舌发出抗争之声。这嘶哑之声正如卡夫卡笔下变形为虫的格里高尔,在无人理解中艰难表达着异化之痛。这种残缺的表达,何尝不是灵魂在重压下顽强不屈的印记?创伤的刻刀将语言割裂成碎片,可每一片碎屑仍执着地映照着灵魂不灭的光。最终,个体创伤的烙印终将汇聚成集体记忆的丰碑。穆旦诗中“带血的手”与整个“站起来的民族”紧紧相拥——个体的伤口竟成为民族创伤记忆的象征性载体。正如历史长卷中,屈原《离骚》中“长太息以掩涕兮”的悲鸣,早已超越个人命运,成为整个民族精神苦难的集体咏叹。每一次带血的拥抱,每一次嘶哑的歌唱,都如刻在民族心灵上的象形文字,将无形之痛铸成不朽的记忆图腾,在时间长廊里反复发出回响。当我们面对沉默或嘶哑的创伤表达时,应心怀敬畏与倾听。在这“正能量”被过度消费的时代,那些破碎的声音与缄默的伤痕,恰如时代最真实的脉搏。这些未能说出的痛楚,这些嘶哑的歌声,是灵魂在暗礁林立的海面上顽强升起的桅杆。它们使痛苦免于沉没于遗忘的深渊,令伤口终能成为精神不息的证明——在暗礁上歌唱,每一缕嘶哑的声波,都是人性在重压下依然倔强迸发的光芒。真正的表达,有时恰在语言折断处——那里,灵魂的印记才得以深刻烙入历史的磐石,成为永不磨灭的碑文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盛达优配官网-股票配资查询-现货配资平台-实盘配资一般不超过多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